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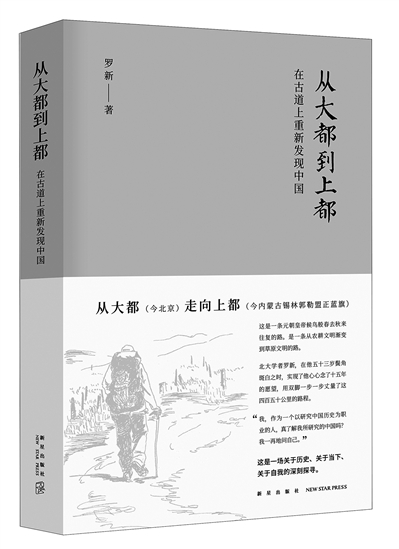
出版:新星出版社
时间:2017年11月
定价:45元
□禾刀
人总是要对自己狠一点,否则,满腹雄心也只会烂在肚子里,逐渐沦为若干年后的惆怅与遗憾。
2016年夏天,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53岁的北大罗新教授咬咬牙,终于实现了15年的夙愿——用15天时间,完成了从大都(北京)到上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金莲川)450公里的田野徒步,并完成了《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徒步就是对生活的抵近观察,本质上也是一种田野式调查,对学者自然更甚。也所以,罗教授才会认为,“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在罗新教授看来,质疑田野徒步的意义,就像质疑阿甘为什么要不停地奔跑一样可笑。
行走就是对社会基层的抵近观察
从大都到上都的这条路,过去只能由皇帝及其随扈行走,也就是所谓的“辇路”。不过辇路并非罗教授浓墨重彩之处,他关心的是,这条联系蒙明两朝的路线,在历史现场曾经扮演过怎样的作用,还有这条路上的百姓与山川,到底还“残存”着怎样的历史信息。
孔子曰:礼失求诸野。相较于上层权力中枢人为式的历史书写,乡野往往是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宝库,许多地名、传说均可能是历史文化的遗珠。罗新教授一路上没有当一名沉默的行走者,他一路观察沿线地形地貌,频繁与村民、基层干部、老人、小贩、服务员、出租车司机等各色人群进行深入的接触,广泛搜集民间信息,结合古诗抑或历史记载,试图从各种碎片信息中拼接出某些不一样的东西。
长城原本是中原用来抵御外敌入侵的军事屏障,也是蒙明势力的一条重要分界线。处于分界线周边的群体,就像是蒙明关系的一条缓冲地带:当两边关系紧张时,这里的人常常利用特殊地理条件,从事走私营生;当关系缓和时,地理优势转瞬丧失,甚至连明朝的那些补贴政策因官员有恃无恐的腐败而难以足额到位。如“隆庆和议(1571年)之后的二十年,是塞内属夷(投靠明朝的蒙古族部落)生活越来越恶化的时期”。另一方面,当年那些跑到蒙古的明朝百姓,因为两边关系缓和,顿时又成了关系回暖的祭品。在历史力量的博弈中,个人命运就是如此脆弱不堪——很少有底层人物能够在政治博弈中始终左右逢源。
蒙明历史关系还清晰地反映到了当地的地貌。除了明朝对元代诸多地名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外,罗新教授还发现,由于关内关外生存方式的迥异,所以呈现的地貌也有很大差别。汉人以种田为主,所以常常会砍伐树木以便整理良田。而那些当初投靠明朝的蒙古族地方边缘势力,不得不放下马鞭羊鞭,像汉人一样下马种田。
有趣的是,长城的功能随着政治角力也会悄然变化。长城修筑于历史,但谁曾想过,在隆庆议和之后,明朝对长城仍旧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修,而许多修筑的动机并不是真正为了抵御蒙古铁骑,而是为了不让那些曾经臣服于大明的“属夷”再度归顺蒙古族,使得明朝失去抵御的屏障。
夹杂在两方力量博弈夹缝中的小人物命运就是这样,交恶时被视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力量,握手言和时,他们则首当其冲成为时代的弃子。
当然,既然是夹缝,自然有夹缝的特别之处。罗新教授发现,民族身份往往只是一张张利益标签,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属夷”,并不见得全都是正统的蒙古族部落,其中不乏因为种种原因逃到那里的汉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常常会给自己取一个蒙古族的名字,一旦获得“属夷”的特殊身份标签,他们立马从受明朝打击的对象变为争取的对象。
行走本质上是对社会的重新发现
行走式体验古已有之。远的如13世纪中叶曾在西方引起轰动的《马可·波罗游记》。
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于1868年9月开始在中国进行了历时四年之久的地理地质考察,足迹遍布中国13个行省”。1877年,李希霍芬将自己的行走结晶成5卷鸿篇巨制:《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许多人对这套书也许不熟悉,但有个词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即“丝绸之路”。正是在这套书的“第一卷中,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在地图上进行了标注”。
虽然李希霍芬当初的行走结论难免夸大之嫌,但许多价值并不能否认,其行走式研究也并不会因此而色泽黯淡。即便在资讯技术早就将世界抹得越来越“平”的今天,行走的意义仍然不可替代。
国内近年来的行走现象日渐升温。罗新教授提到乌鲁木齐铁路局工人刘宇田于1984年从嘉峪关到山海关率先完成长城行走,除了“大长”国人志气外,在研究方面并无建树。而几年后余纯顺的中国行走虽然很火,但仍旧偏重于游历式徒步,成果也只是普通游记。倒是曾在重庆涪陵支教的美国人何伟(Peter Hessler)让人耳目一新。
2011年1月,继《奇石》和《江城》后,何伟的《寻路中国》中文版面世。《寻路中国》既叙述了作者万里行走途中的轶闻趣事,也“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此书出版后,立即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旁观者,何伟的美式思维既看到了社会发展积极的一面,如改革气息几乎弥漫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对一些负面的社会现象也直言不讳,比如不文明的驾车现象,还有让人匪夷所思的租车规矩。
行走是对书本知识与现实的最佳嫁接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罗新教授说:“徒步是对主流的对抗。”只有真正有过行走经历的人,才深知这句话的分量。
罗新教授的这次行走并非真的毫无收获,至少他看到了最为真实的基层现实。他用自己的双眼看到了蒙明边境历史角力留下的许多印迹,许多传统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他还发现一些主流媒体不曾提及的现实,比如偏僻地带个别老穷人员抱着侥幸心理偷种鸦片的现象,还有一些违法现象在基层也被麻木地漠视,而一些基层干部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也颇为肤浅。还有,法律秩序在基层的规范作用有限,一些基层干部对于经济矛盾不是求助于法,而是习惯于寄望强力手段......法律在偏远基层远没有潜规则管用。
罗新教授说:“挣扎多年以后,我们明白了,不是我们成就了旅行,而是旅行成就了我们。”从行走者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行走纵然离不开心血来潮,但一旦踏上征途,意味着的不是简单的丈量距离,而是对书本知识或者脑海印象的一种现实式的再发掘。就像我们久离故乡后,偶尔的一次春节回乡,总会发现许多与自己印象大相径庭的地方。
总而言之,行走就像是用双脚对社会的一次深入解剖。从这层意义上讲,每一个人的每一次行走,都有可能是一次重新发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