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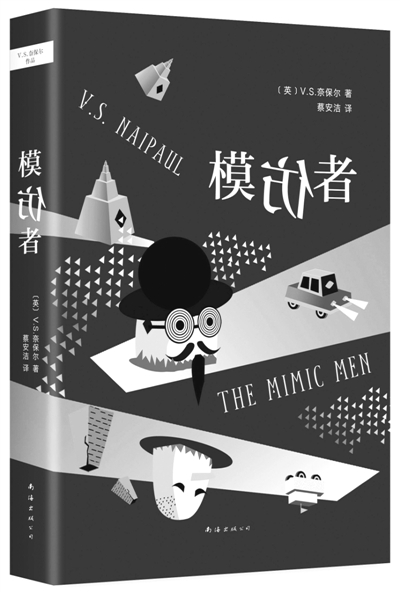
作者:(英)V·S·奈保尔
翻译:蔡安洁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时间:2016年2月
定价:39.5元
□胡艳丽
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以“感谢妓女”石破天惊的奈保尔成了文学界放浪、毒舌、我行我素的一面旗帜,吓得诺奖主席连连声明“我们评奖只看他的作品,不管他的人品。我们爱他的作品,但绝不跟他交朋友”。不论是“此地无银”也好,“掩耳盗铃”也好,关注诺奖、关注世界文学的人听到此言都在窃笑。对于表达灵魂的艺术创作而言,人品和作品之间从来没有清晰的楚河汉界,酷爱嫖娼放浪形骸与“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被压抑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瑞典皇家学院对他作品的颁奖词)之间究竟有何关系?
纵观奈保尔的作品,他戏谑、放浪的影子一直隐约其间,他以放浪对抗混乱,借漂泊消解内心悲苦的身影打动了世人,在“借来的文化中”,纵便才华如奈保尔也始终心存畏惧,缺乏安全感,流浪的感觉贯穿始终。在《模仿者》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他是奈保尔,也是伪政客拉尔夫·辛格,奈保尔以类自传的写法,向他人借来了一段失败的从政经历,把太多自己的情感、认识,投射到拉尔夫身上,在娓娓展开的叙述中,重现了后殖民时期,第三世界的人们在困苦中挣扎,重建秩序无门,左突右支的困境。这是奈保尔作品中一贯的主题,比如《米格尔街》、《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作品连缀在一起,仿若看到奈保尔在其中奔跑呼喊“衣衫褴褛”,却无法趟过混乱之河。
拉尔夫·辛格出生在一个被英国殖民的小岛上,从小受英式教育,和周围的小伙伴一样,盲目的模仿英国式好恶,扮演自己并不了解的角色。长大后到英国学习,却在支离破碎的异国他乡进一步迷失,学会了一身英式皮毛,回到小岛和少年时的伙伴一起,用假大空式的政治口号赢得了岛上的政治地位。然而尘归尘,土归土,舌灿莲花,发泄式地痛斥社会,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他并没有改变现实带来根本变革的能力。对于精神上未能真正脱离殖民、未能形成独立文化,对自我缺乏认同的群体,重建一个新世界又谈何容易?结果早已写在闹剧的开端,对现实无知的政治领袖终要现出原形,政治生涯的终结也是拉尔夫新一轮流浪的开始,于是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可以说奈保尔是个在政治上很不讨喜的人。他批判第三世界国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自身的问题,比如社会文化的苍白、道德规范以及良性秩序的涣散等,都远比曾经被殖民经历带来的伤害更大;他也不认可老牌帝国,在光影迷离的生活之下,深藏着人们精神及情感的虚无,秩序早已破碎。在这种左、右批判中,奈保尔架空了一切世俗的看法,他像一个勇士破开了社会上的主流观点,以率真的文字直抒胸臆。他不人云亦云,不陷入政治臼穴,不为跻身主流社会而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在热闹处看到冷清,在堂皇处看到荒谬,从这一点上说,他是可爱的。
政治不过是社会的一块遮羞布,在文学世界中便是背景底料,它的存在终究还要是映衬人性,让灵魂现形。就《模仿者》来说,书的第一部分,更像是奈保尔的灵魂自白,“来到伦敦,这座伟大的城市,寻找秩序,寻求盛名,寻求在这座光线奇妙的城市里的自我延伸。但是现在我不再知道我是什么;雄心被迷惑,接着淡去。”因为向往、因为未知,辛格视奔赴伦敦为一次新生的机会,然而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缺少方向,走到哪里都注定是浮萍。辛格在伦敦,从一个住处飘向另一个住处,从一个角色飘向另一个角色,从一个女人飘向另一个女人。他努力扮演花花公子、扮演有钱人、扮演放浪形骸,扮演清冷,唯独没有真正做过自己。这并不是一个来自殖民地国家人的特质,在动荡抑或变革的社会中人们都亦如此。比如在中国城市化的大变迁中,一群人夹在城市与乡村中间,夹在南方与北方之间,向前无法融入,有着过去生活的印痕,向后归无可归,田园消隐、人心荒芜。这同样是一个人心飘零流浪的年代。在这种文化、身份的断根与找寻之间,或许模仿是一件安慰心灵的护身符,让人忘记自己的疏离,以表面的相似性获得委身其间的安全感。只是这种错觉麻醉了太多人,令人们在短暂的满足后跌入更深的失落与无望,然后习以为常。
书的第二部分,奈保尔以倒序的笔法,重新回忆了辛格的童年。童年是青年的预演,青年是政治生涯的预演,一切结局早已写在了故事的开端。在没有文化根基、没有自我认同的孤岛上,人们在借来的文化中苦苦辗转,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他们处处模仿英国人的举止行为,表演自己向往却并不了解的角色,连孩子们都不能幸免。儿童的世界是成人世界的翻版,虚伪在孩子们中间传递。读到此处,辛格在伦敦求学期间的种种表现,便有了出处,不过是少年生活的回响。
在求学时期,辛格就已经看透了世俗与政府的虚伪。“人们之间彼此应付,安于套路”、“政客信口开河,无法给人民提供切实的好处”;“我们经常看见那些费尽心思向上爬的人,经过多年的挣扎操控终于靠近梦寐以求的职位,甚至得到了,迎接他们的却是惨痛的失败”。这些似乎已经为后面的从政经历埋下了伏笔。书中的内容互为回声,从少年、青年,到从政再消隐于都市,时间的顺序被打乱,但假若将这些故事折叠起来,从时光的透镜中去窥望,它们都互为翻版,所有的故事都只有一个主题,便是盲目的模仿,而后失败、流浪,文化无依带来的与世界的隔膜从未消除。
拉尔夫·辛格是奈保尔的投影,包括他召妓、放浪在不同的女人之间,对生活不曾付出真心,这一切都是奈保尔式的。所有的这些问题在奈保尔看来都不能归结于道德问题,而是环境使然。对于他这个以文学为使命的人而言,再放浪都是为了体验生活,他“感谢妓女”、感谢在他生命中经过的人,却不为情留恋。在这一点上,他同文学大家索尔·贝娄颇有些相似,他们都需要汲取更多爱的能量,以慰藉漂泊,寻得短暂的安全感,却没有心力持久爱一个人。只是,奈保尔比索尔·贝娄更张扬,也更直接,他对这个世界表达不满毫无遮掩,甚至是自己迎着偏见一头撞上去,任由世人评说,非若如此,他便也不能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恶棍天才”。只是英雄老矣,在拥有“爵士”地位,拥有稳定家庭以后,他的心是否还在印度、特立尼达岛,以及英国之间流浪?还有抵抗世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