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看经济 从经济中看历史
发布时间:2014-01-10 10:15:39 作者:禾刀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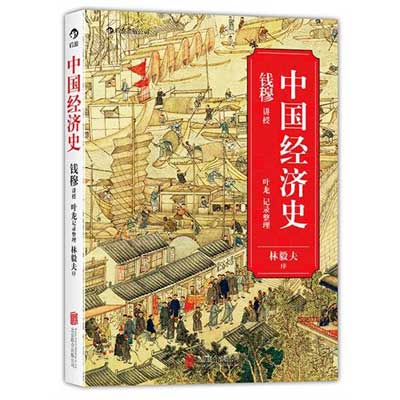
作者:钱穆/讲授
叶龙/记录整理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
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3年12月
定价:39.8元
1954至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曾师从钱穆多年的叶龙,详尽笔录及整理了先师两门课程的内容,并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形成流畅易读的文章,在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最后结集出版形成本书。
有人评价这本书是“从历史中看经济,从经济中看历史”,足见钱穆学识之渊博,本书的主要魅力也蕴含于这句话中。从历史角度看,钱穆对历朝经济史料把握翔实;从经济角度看,钱穆的逻辑分析严谨缜密。
无法摆脱的局限
钱穆曾言,“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乡村,并不安放在都市”。本部著作描绘的中国经济史,主要囊括两大方面,一是历朝农业制度,二是货币制度,其中又以前者为主。或者说,回首中国浩瀚历史,更像是一部农业制度不断变革演绎的历史,从井田、限田、王田、占田到均田,“食”的问题曾被拔高到“天”的高度,成为当权者的最大困扰。唐代虽然推出了租庸调制,“改行两税制”,税赋制度取代了此前过于简单的田地制度,似乎淡化了农业这一主要社会问题,工商业似乎一度得到了较好发育,所以才有丝绸之路,但社会经济的根基依然是农业。
农业问题成了历朝历代无法绕开的重要历史命题。事实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未能摆脱农业大国的历史形象。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工商业才真正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及至今天,虽然国家对农业问题依然高度重视小心翼翼,但经过长足发展的工商业早就成为社会经济体中的绝对支柱,通过继续发展壮大工商业,以便更好地反哺农业、农村、农民,成为决策中心的重要焦点。农业大国虽然没什么不好,但倘若缺乏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经济必然限于市场经济分工低端和经济体量单薄的双重尴尬境地。
不知为何,本书中钱穆对明清经济所言反而显得过于简略。事实上这段时间也正是中国经济首度尝试与国际经济接轨,并最终摆脱数千年重农主义传统的关键时期。特别是晚清,既有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也有张之洞的湖北新政。特别是奠定中国近代工业根基的张之洞,抱定“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思维,照猫画虎地致力于工业建设,寄望于通过复制西方工业发展模式,振兴经济。尽管督鄂17年,张之洞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一批开创国内先河的企业。这些企业虽看似朝气蓬勃,气势宏伟,但终未挽救晚清灭亡的历史宿命。
钱穆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预置了这样一种个人理念,即合理性。也所以,钱穆对历朝经济改革所言甚多,对体制分析甚具。单从改革者的那些理念上看,确似有不少可取之处,但一项制度的看似合理性,并不代表其最终付诸实践后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好的制度只有得到有效落实才能达成初衷。特别是不少朝代慑于“祖制”的威权,对先祖立下的规矩未敢背负“忤逆”之名加以改革,导致原先顺应时势的制度,最终因未能与时俱进,反成制约社会发展的阻力。比如乾隆十四年(1749)全国人口为17749万,而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人口已达36169万,63年时间人口增加18420万,虽然人口增加一倍,但田地住房制度并未能及时更新,于是僧多粥少自然难免。
回首中国经济史,虽然也曾涌现出桑弘羊这样的经济“先驱”。有的施政参政者也曾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比如张居正,但时过境迁,这些改革理念大都难以摆脱历史的局限性,难为今天所用。也许这样要求前人太过苛刻,提出这样的疑问,只是基于另一个思考,即近代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诞生于西方,而非经济总量曾名列当时全球前茅的中国。
基于个体的理性思考
提到现代经济学,就不能不提苏格兰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现代经济学的鼻祖。生于18世纪上半叶的斯密先是于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从伦理学角度厘清了社会关系;1776年,经过反复思考,斯密又推出了著名的《国富论》,也即现代经济学的“圣经”。当欧美人为斯密的经济理念执着疯狂时,我国正值所谓的“乾隆盛世”。也就是那位如今频繁活跃于银幕和荧屏、赚足观众眼球的乾隆皇帝,曾将送上门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视为“奇技淫巧”而拒之门外,并自以为天朝傲视四方。曾有学者测算,乾隆时代清朝GDP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强,但也就是自《国富论》诞生起,西方现代经济体系迅速发育,尤其是以工商业为主的现代经济一路狂飙。70多年后,当经过工业革命并飞速发展的西方国家借助坚船利炮,傲慢地轰开天朝那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国门后,曾不可一世的清朝这才猛然发现,自己原来已被西方国家远远抛在脑后。
斯密的现代经济理论“建模”有一个重要前提,即“理性人”——假设市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换言之,斯密的经济理论着重于每个个体的理性思考,其分析的原点在于一个字——“利”,即私利。
尽管我国历史上不乏经济学家,他们也曾取得过明显成就,但其首要出发点往往在于通过改革,更好地巩固“王权”和“皇权”。虽然民众利益也多被他们一再提及,但这种对民众利益的所谓尊重,从未敢动摇“王权”和“皇权”根基。晚清看似红火的经济改革,也正是由于未能从根本上顺应“理性人”的基本规律,所以注定其努力千疮百孔。虽然“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但张之洞的重工业建设绝大多数处于“亏本的买卖”,张之洞自己也不无感叹,“所成事不过十之二三”。比如曾引以为傲、亚州最大铁厂的汉阳铁厂自建成之日起便处于亏损状态。截至1895年,汉阳铁厂总投资超过588万两白银,但投产前两年所产钢铁仅卖出24825两白银,占投产前两年开支160万辆的1.55%,亏损极其严重。直到盛宣怀接手改为“官督民办”,铁厂经营总算有所起色。
反窥我国历史上的经济改革,无一不以捍卫“王权”和“皇权”为前提,一旦改革影响到社会稳定,改革不仅会开历史倒车,改革者还可能成为平息社会的牺牲者,比如商鞅、桑弘羊。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经济试验均以农业为根基,工商业始终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相较而言,斯密的现代经济理论以个人为研究对象,从尊重个人权益与私利角度为出发点。斯密的研究也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专注于工商业。取向不同,结论自然相异,这大抵就是我国历史上没有斯密的主因所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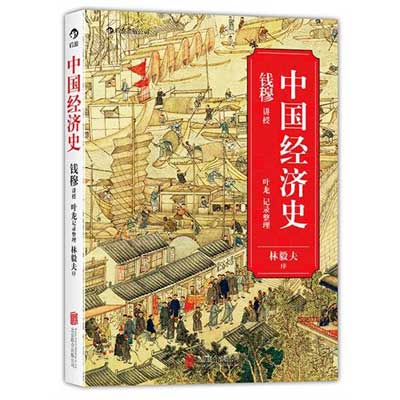
作者:钱穆/讲授
叶龙/记录整理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
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3年12月
定价:39.8元
1954至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曾师从钱穆多年的叶龙,详尽笔录及整理了先师两门课程的内容,并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形成流畅易读的文章,在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最后结集出版形成本书。
有人评价这本书是“从历史中看经济,从经济中看历史”,足见钱穆学识之渊博,本书的主要魅力也蕴含于这句话中。从历史角度看,钱穆对历朝经济史料把握翔实;从经济角度看,钱穆的逻辑分析严谨缜密。
无法摆脱的局限
钱穆曾言,“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乡村,并不安放在都市”。本部著作描绘的中国经济史,主要囊括两大方面,一是历朝农业制度,二是货币制度,其中又以前者为主。或者说,回首中国浩瀚历史,更像是一部农业制度不断变革演绎的历史,从井田、限田、王田、占田到均田,“食”的问题曾被拔高到“天”的高度,成为当权者的最大困扰。唐代虽然推出了租庸调制,“改行两税制”,税赋制度取代了此前过于简单的田地制度,似乎淡化了农业这一主要社会问题,工商业似乎一度得到了较好发育,所以才有丝绸之路,但社会经济的根基依然是农业。
农业问题成了历朝历代无法绕开的重要历史命题。事实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未能摆脱农业大国的历史形象。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工商业才真正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及至今天,虽然国家对农业问题依然高度重视小心翼翼,但经过长足发展的工商业早就成为社会经济体中的绝对支柱,通过继续发展壮大工商业,以便更好地反哺农业、农村、农民,成为决策中心的重要焦点。农业大国虽然没什么不好,但倘若缺乏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经济必然限于市场经济分工低端和经济体量单薄的双重尴尬境地。
不知为何,本书中钱穆对明清经济所言反而显得过于简略。事实上这段时间也正是中国经济首度尝试与国际经济接轨,并最终摆脱数千年重农主义传统的关键时期。特别是晚清,既有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也有张之洞的湖北新政。特别是奠定中国近代工业根基的张之洞,抱定“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思维,照猫画虎地致力于工业建设,寄望于通过复制西方工业发展模式,振兴经济。尽管督鄂17年,张之洞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一批开创国内先河的企业。这些企业虽看似朝气蓬勃,气势宏伟,但终未挽救晚清灭亡的历史宿命。
钱穆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预置了这样一种个人理念,即合理性。也所以,钱穆对历朝经济改革所言甚多,对体制分析甚具。单从改革者的那些理念上看,确似有不少可取之处,但一项制度的看似合理性,并不代表其最终付诸实践后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好的制度只有得到有效落实才能达成初衷。特别是不少朝代慑于“祖制”的威权,对先祖立下的规矩未敢背负“忤逆”之名加以改革,导致原先顺应时势的制度,最终因未能与时俱进,反成制约社会发展的阻力。比如乾隆十四年(1749)全国人口为17749万,而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人口已达36169万,63年时间人口增加18420万,虽然人口增加一倍,但田地住房制度并未能及时更新,于是僧多粥少自然难免。
回首中国经济史,虽然也曾涌现出桑弘羊这样的经济“先驱”。有的施政参政者也曾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比如张居正,但时过境迁,这些改革理念大都难以摆脱历史的局限性,难为今天所用。也许这样要求前人太过苛刻,提出这样的疑问,只是基于另一个思考,即近代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诞生于西方,而非经济总量曾名列当时全球前茅的中国。
基于个体的理性思考
提到现代经济学,就不能不提苏格兰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现代经济学的鼻祖。生于18世纪上半叶的斯密先是于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从伦理学角度厘清了社会关系;1776年,经过反复思考,斯密又推出了著名的《国富论》,也即现代经济学的“圣经”。当欧美人为斯密的经济理念执着疯狂时,我国正值所谓的“乾隆盛世”。也就是那位如今频繁活跃于银幕和荧屏、赚足观众眼球的乾隆皇帝,曾将送上门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视为“奇技淫巧”而拒之门外,并自以为天朝傲视四方。曾有学者测算,乾隆时代清朝GDP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强,但也就是自《国富论》诞生起,西方现代经济体系迅速发育,尤其是以工商业为主的现代经济一路狂飙。70多年后,当经过工业革命并飞速发展的西方国家借助坚船利炮,傲慢地轰开天朝那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国门后,曾不可一世的清朝这才猛然发现,自己原来已被西方国家远远抛在脑后。
斯密的现代经济理论“建模”有一个重要前提,即“理性人”——假设市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换言之,斯密的经济理论着重于每个个体的理性思考,其分析的原点在于一个字——“利”,即私利。
尽管我国历史上不乏经济学家,他们也曾取得过明显成就,但其首要出发点往往在于通过改革,更好地巩固“王权”和“皇权”。虽然民众利益也多被他们一再提及,但这种对民众利益的所谓尊重,从未敢动摇“王权”和“皇权”根基。晚清看似红火的经济改革,也正是由于未能从根本上顺应“理性人”的基本规律,所以注定其努力千疮百孔。虽然“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但张之洞的重工业建设绝大多数处于“亏本的买卖”,张之洞自己也不无感叹,“所成事不过十之二三”。比如曾引以为傲、亚州最大铁厂的汉阳铁厂自建成之日起便处于亏损状态。截至1895年,汉阳铁厂总投资超过588万两白银,但投产前两年所产钢铁仅卖出24825两白银,占投产前两年开支160万辆的1.55%,亏损极其严重。直到盛宣怀接手改为“官督民办”,铁厂经营总算有所起色。
反窥我国历史上的经济改革,无一不以捍卫“王权”和“皇权”为前提,一旦改革影响到社会稳定,改革不仅会开历史倒车,改革者还可能成为平息社会的牺牲者,比如商鞅、桑弘羊。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经济试验均以农业为根基,工商业始终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相较而言,斯密的现代经济理论以个人为研究对象,从尊重个人权益与私利角度为出发点。斯密的研究也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专注于工商业。取向不同,结论自然相异,这大抵就是我国历史上没有斯密的主因所在吧。